香港與新加坡的最大差異是什么?
在談論香港問題的時候,很多人都喜歡將之與新加坡比較一番。
香港與新加坡確實有很多類同之處
兩者均為高度國際化的華人為主的城市
外向型的小型經濟體
人口密集而天然資源稟賦不足
同受英國殖民統治影響等等
近幾年來,香港社會在討論土地規劃、房屋制度、產業政策和人才吸納政策的時候,越來越多人視新加坡為「學習對象」。
但回顧幾十年前,情況卻是調轉過來,香港曾經長期是新加坡模仿的榜樣。已故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在其自傳中透露, 1965 年獨立之后,他幾乎每年都會到香港一趟,看看香港人「如何克服困難」,以及有什么值得學習的地方。
他直言,香港是他「獲得靈感和啟發的源泉」,亦十分欣賞香港人的勤奮、活力和干勁,認為香港不但「價廉物美」,而且「服務一流」。
人均GDP逐漸拋離
上世紀 60、70 年代的時候,新加坡無論在經濟規模、人均 GDP 、金融等專業服務業水平、甚至制造業實力等方面通通不如香港。
但到了 90 年代,香港與新加坡已經處于同一水平線上。自 2003 年起,新加坡人均 GDP 超越香港后便一直將香港拋離。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的預測估算, 2021 年新加坡和香港的人均 GDP 分別為 66,263 美元和 49,485 美元,差距明顯;如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人均 GDP 的話,新加坡達到 102,742 美元,香港則只有 62,839 美元。
除了經濟增長方面,新加坡在產業結構上也比香港更為多元化。
2020 年,其制造業依然能維持在 GDP 的 20% 以上。而香港的制造業卻不斷萎縮,如今只占本地 GDP 的 1% 左右。
新加坡目前是全球第三大煉油中心,其電子工業和生物醫藥等高增值制造業亦有相當實力,同制造業空心化的香港形成巨大的對比。
新加坡有不少社會政策和公共服務也把香港「比下去」。
住房方面,新加坡國民的置業率接近九成,香港的置業率在過去幾年則徘徊在 50% 左右。
醫療方面, 2019 年新加坡有 14,279 名注冊醫生,每 1,000 人有 2.5 個醫生,當中 67% 注冊醫生在公立醫院工作;2019 年香港注冊醫生人數為 15,004 人,每 1,000 人有 2.0 個醫生,當中約 50% 注冊醫生在公立醫院工作,但實際上承受服務全港 90% 住院病人的壓力。
新加坡組屋平均面積為 1,067 平方呎,平均價格為 53.27 萬新加坡元(約 306.8 萬港元),可稱得上為「價廉物美」。
新加坡的人均居住面積有 323 平方呎,比香港私人住宅單位的人均面積中位數( 194 平方呎)還要高出 1.66 倍。
新加坡并沒有土地短缺而急需「造地」的問題,因為 1966 年頒布的《土地征收法》規定,新加坡政府可出于公共利益強制征地,并將賠償金額限定在固定的較低水平,以保障政府以低價獲取大量土地以進行更好的城市規劃。
同時,新加坡政府通過明確的產業政策引導經濟發展。
1990 年代,新加坡已開始謀劃引入半導體產業,其經濟發展局為每一個有意到新加坡投資的半導體公司提供從投資建廠前規劃評估,到建廠中的水、電、土地取得,甚至是完工后的人員招募、長遠的財務規劃等一系列協助。
輸外勞遏服務業工資
煉油石化產業亦是很典型的例子。新加坡的一個天然優勢是位處馬六甲海峽,即東亞和中東、歐洲之間的重要海上通道。
新加坡雖然沒有任何石油儲備,但得益于作為海上石油通道的地理優勢, 60 年代起,新加坡開始布局石化產業,通過多項優惠政策吸引跨國石油公司在新加坡設立原油加工廠,促進資金和技術轉移.至今已聚集超過 100 家跨國化工企業,僅次美國休斯敦和荷蘭鹿特丹成為世界第三大煉油中心。
在此基礎上,新加坡亦藉助其金融和航運業的既有實力,將自己定位成亞洲石油產品定價中心和世界石油貿易樞紐,進一步提升新加坡參與跨國經濟活動的影響力。
新加坡還有一個「致勝法寶」,就是通過大量輸入外勞,將消費性服務業的工資維持在一個相對較低的水平, 因此新加坡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 GDP 才會遠高于香港乃至美國。
同時,新加坡制造業的競爭力亦是通過輸入外勞來填補較低技術工人的空缺,將高附加值職位騰空予新加坡國民。
新加坡常住人口約 570 萬人,而當中外勞占超過 150 萬;一定程度上,新加坡是通過剝削外勞來維持其本國產業的競爭力。
前一段時間新冠肺炎在新加坡爆發,亦暴露新加坡外勞的生活環境擠迫惡劣的問題,
以上各方面都是新加坡與香港的差異所在。
但歸根到底,新加坡與香港最大的分別就是新加坡有一個強勢政府,能夠有效平衡各種社會利益團體,高效地使用和分配社會資源。
建國經歷種種紛爭
新加坡同香港一樣承接了英國人留下的公務員系統,從行政能力和廉潔程度來說,兩地其實不相伯仲。
但兩個政府之所以差別很大,是因為新加坡自建國以來通過艱難的政權建設的過程才走到今天。而香港從殖民政府過渡到特區政府的過程中,卻沒有經歷過一個新政權建設的過程。因此兩個政府在政治能力上顯現很大的差距。
新加坡建國初期,經濟條件惡劣,對內面臨左翼政黨的挑戰,對外面臨與馬來西亞的族群紛爭。
人民行動黨與新加坡國內外的利益進行斗爭,包括以殘酷手段鎮壓左翼運動,以及在國際社會中確立新加坡作為一個新政權的地位。
是通過這樣的一個過程,新加坡內部才能形成一個強而有力的執政力量,也就是現在我們所見的人民行動黨政府。
人民行動黨的其中一個成功條件,是對其生存有著強烈的危機感。

2019 年香港出現反修例風波,輿論認為新加坡是受益者,應該是一種「隔岸觀火」的態度。
然而,總理李顯龍在接受采訪時卻表示,他其實非常擔憂如果類似事件發生在新加坡應當如何應對。
新加坡其實比香港「更脆弱」,呼吁國民警惕可能導致社會撕裂的力量和事件,并為與這些力量抗衡做好準備。
反觀香港,回歸過渡期更多地是強調如何將港英時期的行政體制平穩過度到新成立的「香港特區政權」,但回歸前后都缺乏真正意義上的新政權建設。
而回歸后的留下行政系統雖然具備行政能力,但在利益錯綜復雜的香港社會中并沒有足夠的號召力和影響力,更遑論應對香港自由開放的復雜政治環境。由此導致特區政府的政治弱勢,難以積聚政治領導力。
一個強勢政府背后實際上是政權的政治能力,而這才是香港同新加坡的核心差異所在。
當社會上主張香港學習新加坡的時候,不能只是表面地參考新加坡的具體政策,更重要的是特區政府如何完善政權建設,通過克服社會上的不同利益要求,引領整體社會的發展方向。
否則,再多的政策設計而缺乏政治能力,香港仍然難以解決積存多年的社會深層次矛盾。
實際上,在香港回歸的一刻,香港特別行政區就屬于國家治理體系的一部分。
2019 年 11 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有關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決定中,已經把完善「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治理體系納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部分。
尤其是落實《港區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之后,香港接下來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國家領導下完成特別行政區的政權建設,強化特區政府政權在香港社會的基礎,「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才能行穩致遠。
END
來源丨簡思智庫
作者丨方舟,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
版權說明丨緯博海外家辦尊重原創,版權為原作者所有,若侵權,我們會及時聲明或刪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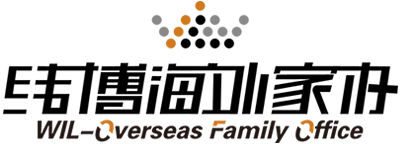

 粵公網安備 44030402004578號
粵公網安備 44030402004578號